何凤山的“中国梦”
时间: 2014-08-22 11:08
崔述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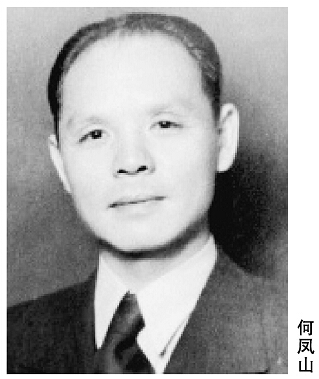
2000年冬天,我拜访回湘省亲的旧金山侨领钟武雄先生。钟先生借给我一本他姐夫、号称“中国辛德勒”的何凤山所著的《外交生涯四十年》。我因之开始了解何凤山。2001年9月上旬,我应益阳市政府之邀请,去参加何凤山百年诞辰纪念活动。之前,曾陪同钟武雄先生去长沙黄花机场,迎接由美返湘的何凤山之子何曼德院士。何曼德知我借了钟先生的书后,即向香港邮购了两册书,寄给我。分别送给我和我供职的湖南图书馆。翌年夏天,何曼德将其大著《我的教育,我的医学之路》也题签了两册邮寄给我,并请我帮他了解在故国、家乡出版事宜。
依我10多年来与何曼德先生的交往,了解到何凤山、何曼德父子俩都有一颗“中国心”,皆有“中国梦”,而且跨世纪、逾千年,至今犹在延续。复读何著《外交生涯四十年》,我从中读到了何凤山的“梦”,他的梦的破灭,他的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
何凤山谢世于1997年9月28日。何曼德曾在台湾《湖南文献》上,“吁请”为其父“平反”,洗清莫须有的“不白”之冤。文中所述何凤山晚年生活之不尽如人意,确实令人扼腕。
何凤山不仅是中国国民党,及其老“总统”、蒋总裁的不二忠臣,更是给“海峡两岸中国人”(如1972年中美的三个“联合公报”文件中所言)加分的“国际正义人士”“中国辛德勒”,是华人之光、之傲,但这位集“忠臣、义士”于一身的湖南人,却因自己的愚忠、盲信,以及湖南人性格的“缺陷”,且被他却发挥到“极致”,而导致了这种每况愈下的命运、宿命。
何凤山去世时,唯一的慰藉是,他看到了香港回归。 何凤山在抗战胜利后,对香港未能归还祖国,又“转手”交给英国,是非常不满的。何著《外交生涯四十年》第201页中记述道:1946年9月中旬,为“九龙城内(中国)‘治权’事”,何凤山再次执拗着,强出了一次(风)头。他绝对是一位爱国的、有民族正义感和凛然气节的中国官员。但他却不该,也不顾官场上的原则和禁忌,为国事而冲、顶、撞,因而得罪、冒犯了一些人。当时,何为抗议港英当局,邀叶公超联名进言其上司、外交部部长王世杰。叶公超时任欧洲司长,推诿说,要见美国大使,没有时间。但何凤山却坚持要在秘书室等他,且“不能再忍受”地对叶氏“晓之以理”地说:“国家领土的事,大事也!”我固担当不起,部长的责任犹大,更不能不了了之!在这位“霸蛮”的湖南人坚持下,叶公超“仿佛在赌气似的”,将(何)文中某段圈掉后……批准。
次日,在“各报章上发表”的,占据“头条”的,当然是这位“外交部发言人”的大名,令民众联想起他义正词严的声态和身影。虽说亦有粤省某特派员一人向他表示感谢(因此事帮其解了围),但何凤山潜越之举,又得罪了上至部长下至叶公超等一批人。谁又会不懂国家大事呢?外交部的人,谁又不知“外交无小事”呢?
究竟是不是这个原因?但结果是,抗战时,窝在山城的何凤山,不久即被外放到埃及去当公使了。为了国家大事,牺牲了小我的何凤山,几十年后又怎不会为香港整体回归中国而高兴呢?我想,任何自视为华人者,莫不如此吧。
尽管何凤山在埃及独当一面,任职期间全力以赴,为“党国”而身先士卒。但到了50年代初,“大势”去矣。任凭他这使馆的“大树”“中军旗”未倒,其属下却自谋退路或出路去了。就连昔日的反共斗士“西北王”马步芳,这位有阿拉伯血统,有“异相”如安禄山者,都兵败如山倒,带着多年搜刮的钱财,跑到国外当寓公了。而看不起这些军阀无人品、无国格的何大使,却仍然忠实于他的“党国”。当何凤山与昔日反共“悍将”马步芳交谈时,后者也认为“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事”。但这位“粗中有细”素有二心的马步芳,却不忘利用使馆这个“平台”,利用何凤山苦心经营,在埃及构建起来的“人脉”,作秀、造假、拍照片,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。蒋介石竟然还奖给马氏一万美金。而何凤山愚忠的结果,却是黯然撤离埃及。他可能自认为“国难”见忠臣,自己从来不发国难财,不得不义之财,不见利忘义。但事隔多年后,犹被那些“惦记”着他“嫉恶如仇”的“洁癖”的人,泼污水、污名化。
何著只写至他再次“被撤离”驻墨西哥使馆为止,而略去了以后出使的情况。像他这样一位清白的人,“蒙羞”乃奇耻大辱,属难言的终生隐痛。
话说回来,蒋介石对何凤山还是“知人善用”的。蒋介石岂止了解?而是深知何凤山重名誉不重实利的“软肋”。这位领袖,可以对唐生明那位被他派到汪伪政权当“卧底”的“四公子”,在抗战胜利后,一次赏给几倍于警察局的奖金;也可以在缺钱的时候,给放弃职守的马步芳一笔钱。因为这两人都是要钱,而且舍得挥霍,会花钱的。至于“何大使”,每次回“国”“述职”时,请他吃饭就得了。何大使的“官越做越小。暮年的老蒋,形同“太上皇”,他虽想撮合、弥合何凤山与蒋经国的人的关系,但也是“势不能穿鲁缟”矣。因为,如所言——
1950年5月16日,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,何凤山等人撤离前夕,“美国特务人员经武官介绍,向我请求,在馆内预装窃听器,我……思索后回绝了”。美方警告说:“你应该知道……我们已得到了你最高××的应许”。何凤山一听,傲脾气又犯了,说:“身为大使,只听总统蒋公与外交部的命令……××并没有告诉我什么……”何凤山更不该画蛇添足地补一句:“我与他没有工作上的关系,用不着问!”“而“太子”小蒋,其时,“正掌握着台湾特务大权……自然(对我)不满,种下了对我不利的主因”。
何凤山返台,蒋介石赐宴,让其子作陪时,老蒋虽一再说“经国,你不妨和何大使谈谈”。蒋经国都充耳不闻。而以“老臣”自居的何凤山,也傲然却徒劳空等着“小蒋”向他“请益”。这两人又怎会“握手言欢”呢?
何凤山在必然的蒙冤和备受冷落后,终老于美国。其实他心中也是非常憋屈和不得已的,姑且抛开“晚景”之黯淡等表面的,生活方面的原因,让我们看看他书中196页的一段话吧:
8月14日(即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同日)签订“中苏友好条约”……后,以上事实看来(外蒙独立及战后苏俄在华特权的恢复及扩大的)“雅尔塔密约”,无论在道义上与法理上,对中国都不能发生任何约束力,政府……应马上抗议。国家领土权益问题是何等大事!应指出美国的作为是违反了“开罗宣言”,侵犯了中国的权益与领土完整。
“雅尔塔密约”使中国签订了丧权卖国的中苏条约……美国方面不过在其外交历史上多加了一件出卖盟友的纪录而已。
何凤山还进一步指出“国府错在一个‘怕’字,而失理智,连普通外交常识都丢了……张国焘云:毛泽东讥蒋介石与国民党有‘阿Q精神’”。这阴魂已成我们(台湾)的国魂。”请注意,最后一句是何凤山的结论。要是回到过去,他是绝对不会引用一个他看不起的共产党的叛徒,所引用的‘共党’领袖毛泽东的挖苦国民党的话,更不会对他的蒋公大不敬的。他没有为尊者讳,为逝者讳,是他在晚年的“彻悟”。要不然,为什么会在隔离近四十年后,他在悄然回到家乡湖南益阳时,会在“欧美同学会”上说:“统一是大势所趋”呢?何凤山是从不说违心的假话的,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,他也是一位耿直敢言的湖南人。“分久必合”,两岸统一是他的梦想,是他的“中国梦”。时至今日,我们是应该抛弃小我,不计前嫌,不为个人,也不为自己所属的政党,而是为海峡两岸人民的福祉,而奋斗的时候了。
何凤山言之有理,且有预见性。当年的战胜国,“四强”之一,在其他“三强”的霸道和强权之下,实际上连“失土”都不能收回,形同战败国,名胜实败,留下了日后钓鱼岛的纷争等领土的归属问题。我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、全世界的华人都可从何凤山这位“前车之鉴”的“绝唱”中,觉悟到我们只有避免“兄弟阋于墙”,才能共御外侮。
而“中国辛德勒”的儿子何曼德,亦曾在台湾“绿营”的《自由时报》上,表明过“我深信台湾人,是十足的中国人,台湾的历史文化,是广义的中国的一部分。我觉得这是不可否认的……二十年以来,大陆许多方面有意想不到的进步,让人很难预测他二三十年以后,会演变到什么地步……希望两岸可以根据共同的文化,形成一个可以互相学习、交流、互相砥砺的‘一个中国’”。
何曼德几岁时,就随其父何凤山赴土耳其、奥地利,他通晓多国语言,却自愿选择了回中国念中学和大学。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。尽管几十年来一直沐浴着“欧风美雨”,他仍然觉得“中国文化并不是最古的,但却是世界上政体完整性持续最久的国家,这个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”(见何曼德《我的教育,我的医学之路》)。
以他的民族、国家观来看中国形成的历史,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,通过也认同它优秀的,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向外传播,才融合而成中华民族,并向外辐射到五大洲。中华文化是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软实力。
反倒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疆域和领土,自元朝、清朝和民国以降,一直在被分裂,被萎缩。甚至连邻近的一些国家,至今仍在蚕食中国的边疆和海疆。特别是二战的战败国日本。尽管中国领土上的当政者都宽容的放弃了战争索赔,放弃了战胜国应有的驻军日本的权利。而日本却通过《旧金山和约》,以及美国人的私相授绶,非法且无效地窃据了原有“国军”驻扎过、一度辟为“国军”靶场的钓鱼岛。
中国从千百年来被包围、被侵略的历史中,懂得了“唇亡齿寒”的道理,曾在二战中组成远征军,驰援缅、印,解救英军;1949年后又支援过两个邻国反侵略的战争。当中国反遭侵略时,中国亦如历史上一样采取驱赶、教训的对策。更有甚者的是,战而胜之后主动撤军,至今未在外国领土上驻扎一兵一卒。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,中国和何凤山这样的中国人,都是同情弱者的。从孙中山曾想以中国之某岛,安置犹太人。到何凤山在奥地利,向犹太人颁发“生命签证”,无不证明中国及其人民是爱好和平的,是善良且极富同情心的。
海峡两岸中国人,五洲四海的华人、华侨,只有排除私心,“相逢一笑眠恩仇”,超越党派和族群的利益,联手连心,才能共圆民富国强、天下太平、四邻和睦相处的“梦”。弱国无外交。当年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,尽管其能力超群,但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,也是徒劳无补,空有抱负而已。
(作者单位:湖南图书馆)
链接:
中国“辛德勒”何凤山
美国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德国商人辛德勒冒险拯救犹太人的故事。其实,辛德勒的故事也曾发生在一名中国外交官身上。这位外交官就是何凤山。
1938年底至1939年初,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身陷“人间地狱”。腥风血雨中,一艘轮船冲破死亡封锁线,往返七趟,载着3600名犹太难民驶往远在东方的中国上海。上海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大城市。顶峰时,曾有3万余名犹太人在上海避难。上世纪末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“犹太人在中国”展览会上,二战期间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签发数千份“救命签证”救助犹太难民的历史资料首度被公开,人们终于找到了当年牵引方舟的救命恩人。2000年4月1日,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“外交救命恩人”展览再次展出了何凤山的事迹。何的义举受到了以色列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褒奖。
何凤山,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,1926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,1932年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,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,1935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,1938年出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,1940年调离维也纳后仍在外交界供职。1973年,何凤山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,专心学问,著有《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》。1997年9月28日,何凤山去世,享年96岁,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曾派代表前往致哀。
(本刊资料室)


 湘公网安备43010502000525号
湘公网安备43010502000525号